
刘瑞莲
文艺界任何一个心存虔诚的人,若要为山东曲艺写史作传,“曲艺窝”菏泽,都将会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若将这“浓墨重彩”人格化,便是一串被人们挂在嘴边上的曲艺家名字。此言绝非夸张。那一日,我在文化厅参加山东报送全国“群星奖”节目的评审,与参评的音乐、舞蹈、戏剧比较,曲艺显然相形见绌,不尽人意。面对众评委的议论质询,我的回答声嘶力竭:曲艺是靠韵味夺人,而“韵味”不可能少年有成,正因为它是“成年艺术”的缘故,在急于求成的“造星时代”,倘若火暴反而失常。不想,我的“强词夺理”竟得到舞蹈编导胡玉平先生的积极响应,他大声说道,曲艺靠韵味夺人不假,今年春晚录音,遇到菏泽一唱坠子的“女曲艺”,她开口一嗓,便让噪杂的前厅一片肃穆,听“流行歌”长大的年轻人哪里晓得有这等天籁之音?这位“女曲艺” 几句便将这些后生的“魂”钩走,录音棚当时静得竟像无人一般。想,这人你定认识……
“刘瑞莲”——身边几位评委几乎与我一起将“她”说出。
如此,不足为奇。当下山东演唱河南坠子开口能将人“黏糊住”的,除了菏泽的刘氏瑞莲还能有谁?!只是,切莫以为说这,我便为山东曲艺有了这刘氏女沾沾自喜、一身轻松;恰恰相反,那时间我的心灵竟似坠上铅块一般沉重无比。想想看,这“韵味”也好,“情趣”也罢,本是曲艺有别于其它而独立生存之“魂”,当年靠“它”,山东观众硬是将“郭文秋”等河南坠子大家,打造成了山东曲艺享誉全国的文化品牌。时过境迁,今天提到“河南坠子”的魅力、韵味,人们所能想起和喊出的就一个“刘瑞莲”了。悲乎?喜乎?还须赘言乎?!
正是这“忧患”,激发了我对以菏泽为“中轴”,始终活跃在中原乃至中国曲坛的刘氏瑞莲及其河南坠子艺术“深入”的兴致,几个昼夜后,零散记忆中的刘瑞莲从我“眼前”渐渐完整而清晰起来——
若将刘瑞莲留给我的印象强力浓缩,让我脱口而出地第一个字是,“梦”。切莫小看这个“梦”字,要我说,当下曲艺界乃至整个文艺界真正有“梦”的人极少,尤其像刘瑞莲这种年过四十依然对艺术心存敬重、以至于魂牵梦萦的主则更是凤毛麟角。梦是什么?是幻想、理想、目标、希望,是未来引导我们去的地方。在物欲横流的年代,对物质享受怀有“梦想”的大有人在,而比这“大有人在”还要“大有人在”许多的是,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与满足,更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对“精神梦想”的放弃。君不见,文艺界时下最流行“平淡自慰法”,即把对物质生活要求的高境界“知足”、“平淡”,混淆到精神领域,使之成为一种对艺术、对专业“不思进取”的托词、理由。因工作缘故,我大多时间都在山东“文艺圈”转悠,听到最多的就是“我现在可好了”,之后便是“买房买车”、“孩子工作”一类的“家妇语言”。正是徘徊在这样一个“精神失语”、或者说“艺术少梦”的时空中,我对这位对河南坠子矢志不移,每每见面便要我帮她引荐一位艺术大家为“师”的刘瑞莲,不得不刮目相看。因为有梦,刘瑞莲的才有可能“梦笔生花”,让她的河南坠子唱响中原。其实,后来我才得知,刘瑞莲对河南坠子早已是“梦魂颠倒”,在情窦初开的少女时代,她便发誓要找一个“会写词儿”的文人为夫,不管年龄大小、模样丑俊,只要爱她的河南坠子,她都会与他牵手终生。用她的话说,“我们家几代从艺,从我姥姥、姥爷到我老娘,全是唱河南坠子的,河南坠子要想生存、发展离不开文化人的掺和呀,新凤霞的《花为媒》,没有吴祖光的词儿能成吗?豫剧大师常香玉身后不也是有一位有文化、会写词儿的老公给她撑着呀?!”她这些“说辞”的对于否当然有待论证,但我被感动得是瑞莲“为梦殉情”的敢作敢为。每逢有演出或比赛,听到她那“钩人心魄”的坠子腔,看到站在领奖台前列抿嘴微笑的她,浮现在我脑海的总是一些记不起在哪里读过的“名家名言”:“那种在实际生活中即使一败涂地还始终如一地保持幻想和憧憬的人,才是真正的幸运儿。”“在走向人生这个征途中,最重要的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地位,而是在自己胸中像火焰一般熊熊燃起的一念,即‘希望’。”“如果你能找到激励起自己执着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
其实,没有梦,失去前瞻,失去创造,生活便失去了诗情,人也就失去了称之为人的生命。想到这些,竟生发出些茅塞顿开的“感应”:我们民族曲艺之“韵味”不恰是生活之“诗情”一种艺术化的呈现么?!
“思”,是我从刘瑞莲及其河南坠子艺术中悟出的第二字。热情取代不了科学,这是做事从业所要把握的最基本、最本质的规律。本来我是将刘瑞莲看得浅显了,因为彼此太熟悉,则往往容易被假相或表象所迷惑,她给我的“假相”不过是一位“实践大于思想”的曲坛“虎将”而已。殊不知,与她简短交谈便让我大呼“上当”,她对艺术、对曲艺、对河南坠子竟有相当的“思想”。比如,谈到菏泽曲艺、谈到自己,她看得最重的是“根”与“土”之间的彼此作用,她说,“菏泽曲艺队解散,我被安排在生产资料公司看大门,名义上看了20年,其实,我和我的坠子一天也没分开,上到首都北京、省城济南,下到菏泽的各县、乡镇,只要有演出、有比赛我一个也没拉下。别人都盯着‘钱’,我盯着‘演’。我丢不下观众,观众才舍不得我。你想想,你与观众一天都没分开,与时俱进不也就‘化’在其中了吗?”品一品,咂咂味,这个“化”字,何等了得。刘瑞莲曾拜托我为她寻求一位“名师”,我问她为何不拜家居省城、名扬华夏曲坛的坠子大家郭文秋?她忙说,不成,不是一路,我接触和形成的那些东西与郭老师风格差异太大。为了摆脱尴尬,我顺她“思路”而下,说,对啊,你唱得多是让人流泪的悲伤之作,而文秋先生风格则是俏皮、欢快。不想,她却没给我面子:“郭老师唱《王二姐思夫》、《黛玉悲秋》这些苦段子也很棒,我‘偷’了她许多,其实我‘偷’人家的玩意多了,不过可能除了被我‘偷’的人之外,一般都听不出来。”由此,我在心中愈发欣赏她的“有心”,可见她绝不是曲坛流行的“拜师拜名”一族,而是一个懂得“知己知彼”、“量体裁衣”、“化他为我”等规律的明白人。其实今天曲艺界,在名利上下功夫的“有心人”不缺,然,大缺特缺缺的则是刘瑞莲这种尊重规律,且懂得“顺应规律谋发展”的曲艺家。
无疑,我们今天曲艺之整体处在一种理性思维“混沌”的状态。我曾以“当下曲艺少思想”为题在一会议作过发言,所谓“少思想”,我是指曲艺对自己发展缺少清晰思路而言。我想,曲艺之整体当然是由每个个体组成,倘若我们的曲艺家对自己的发展有了科学的、清晰的思路,那么我们的曲艺之整体又何愁没有思想与智慧。因为,没有什么比思想再重要了,它是力量之源,心灵之泉。只有让思想的太阳高高升起,这样,不只是我们每一个曲艺家,而是我们整个民族曲艺都将会得到滋养、丰富而发展。
我还想到,曲艺之韵味,不同样是曲艺家一种“思想”的返照么?!因为“思想是不容易察觉的,因为它们是我们思考的工具而不是思考的结果,犹如你能够看到外界的东西而不能看到你用来看东西的眼睛一样。”
“刘瑞莲”告诉我的第三个字为,“恒”。因为有“梦”托着,因为有“思”引领,所以刘瑞莲和她的河南坠子艺术具备有足够的耐力与韧劲,最终使她与它在老百姓中“威信”得以持恒。
先说点题外的话。近日,我的“博客”突然热闹起来,有部分酷爱曲艺的有识之士,“逼”着我对今日“传统”与“现代”两种曲艺“叙述方式”发表看法。于是,我便有了以下的文字:听曲艺、看曲艺,听啥?又看啥?概而括之:趣与味。可是姜昆、冯巩,包括我们的唐爱国等,他们用他们的曲艺、相声改变了观众的欣赏习惯;当然,我们更可以说,是观众欣赏情趣的变化“逼”得他们改变了曲艺、相声的“叙述方式”——他们用“事”儿、用作品的“信息量”替代了当年观众欣赏曲艺(或相当一部分观众)的追求——“趣与味”。如果我们把“拓展观众群”比喻为“打井找水”,这类“曲艺”基本属于是“横向寻水”,即对“传统”或许“挖”得浅,但挖得面积却“广”,且“出水率”(观众群)极高;而像侯宝林等这些“老先生”属于沿着传统“竖着挖水型”的,因为“挖”得深,则水也很多。横着挖水,浅而广,则容易“风干”;竖着打井,深而窄,却不易“风干”。再就是,“横着行”习惯了,容易侵占“别人领土”,结果或是吃掉别人,或是被别人吃掉(曲艺家已经被电影吃掉很多了);而“竖着打”则宜于“安居乐业”,当然也容易“小康即安”,而不思进取。
我想,若给刘瑞莲划类,她和她的河南坠子显然属于“竖着挖水型”的,只是她长期不间断地坚持演出,始终“生与活”在民间,则又有些“靠水养水”的形态。所以,刘瑞莲的成才之路似乎更带有一些曲艺“本质性”规律的特征。
据我所知,刘瑞莲的这些年的生活充满坎坷,非常之不易。当听说,她终于在20年之后,被当作菏泽文艺界出类拔萃的人才被菏泽市“特事特办”,已到了群众艺术馆上班的时候,眼瞅案头一大摞她“坠子集”的书稿,我耳畔回响的竟是与这“欢快”有极大反差的一个伟人的声音:“我们完全可以以苦难而自豪。须知,苦难生坚忍,坚忍生品质,品质生希望,而希望是不会让人消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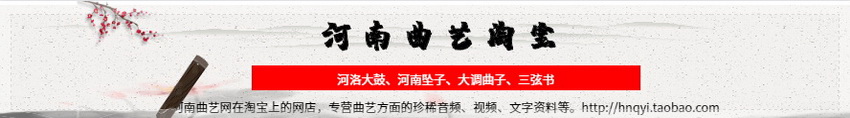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