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廿三

活灵活现活口书
尽管此前对刘大江说的书很佩服,但还是低估他的能力了。刘大江的本事远远不止这些,随着说书的深入,更觉得他不是一般的“能人”,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说家儿。
还回到上一章的情节。上回书我唱到王贵派人把宋仁宗绑到法场,午时三刻,大炮三声就要人头落地。有的说,午时三刻是啥时候?古时人们把一天一夜划为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俩小时,从夜里十一点至一点为子时,白天十一点至一点为午时,十二点为正当午时。一时分八刻,又分为初刻和正刻。午时三刻指的是正三刻,就是现在的十二点四十五分。
古代为啥要选择午时三刻杀人行刑呢?午时三刻是太阳挂在天空正中,是地面上阴影最短,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刻。古代迷信说法,认为杀人是“阴事”,害怕被杀的鬼魂来纠缠监斩官和刽子手。所以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制阴气,使鬼魂冲散,不能害人。这应该是古人习惯在“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话说大炮已经响过两声,正准备响第三声,只要再响一声,我就把老宋给送到鬼门关啦。把大宋的皇帝给说死,祸可就闯大了。幸亏想起来得早,第三炮没响出来,立即悬崖勒马,来一个急刹车,搁住了。
我擦了擦头上的说不清是热汗,还是冷汗,向刘大江耳语:“刘先儿,给你扒这个豁子可不小吧?看你咋补。”
刘大江笑笑:“你把张宝童搬兵的事儿给吃啦?”
我说:“没有吃,是忘啦。头一次说大书,顾着这头忘了那头。我说不敢说(书)吧,你非叫说,这窟窿你想办法补吧,我不管啦。”
刘大江笑了笑:“看把你愁的,这窟窿还能补不住?你不用管,交给我啦。”
刘大江不愧是高手,只见他不慌不忙,面不改色心不跳,从从容容,轻易而举地就把这个漏洞给堵住了。他接着这样唱:
……宋仁宗绑到法场上,午时三刻问斩刑。第一声大炮天地动,第二声大炮鬼神惊,法场上放罢两声炮,只惊得五方神灵不安生。李金星打坐斗牛宫,只觉得耳热眼跳不安宁。哪里天高不下雨,哪里旱涝减收成,哪里困住忠良将,哪里妖怪胡乱行。李长庚屈指只一算,不好了,陈州城困住了紫微星。紫微星有难我不救,玉皇爷怪罪下来了不成!想到此处不怠慢,急慌忙离了斗牛宫,一驾云头八千里,眨眼间就看见陈州城。眼看看牛时三刻就要到,急坏了太白李金星。钉阳神针拿在手,照着太阳猛一扔,只听得噌地一声响,把太阳钉在正天空。钉住太阳不会动,午时三刻到不成……
哈哈,还是刘先儿神通广大,危难之际,来不及叫张宝童搬兵,就先把太白金星他老人家给搬来啦。李金星有本事呀,把太阳给钉住了,动弹不得。
有的说,可拉倒吧。把太阳钉住不会动了,把钟表的时针也给钉住啦?你傻呀,那个时候哪来的钟表。人们都是看太阳的影子做标记来定时间的。太阳不会动,午时三刻就不会到;午时三刻不会到,第三声大炮就不会响;第三声大炮不会响,三盏阴魂灯就不会灭;三盏阴魂灯不灭,宋仁宗就不会死;宋仁宗不会死,就给张宝童搬兵赢来了时间。就这样,看似无回天之力的事儿,被刘大江三言两语,轻松地给化解了。
而补这个窟窿,刘大江做得几乎天衣无缝,毫无破绽,让听众听不起来任何缝补和斧凿的痕迹,这就是人家的高明之处。
撒罢书后,躺在床上,还在议论此事儿。刘大江说:“幸亏你没把第三声炮放响,如果放响了,还真有点棘手哩。”
我一听,较起了劲儿:“刘先儿,我要是嘴再快一点儿,万一……我说的是万一,把第三声炮放响了咋办?”
刘大江说:“你嘴再快,再不考虑,总不会让刀斧手把皇帝的脑袋给割了吧?只要宋仁宗脑袋不掉,我就有办法补救。比如让土地爷韩文公带着小鬼儿小判儿来,使一个定刀法把刀斧手的刀给定住,不就死不了啦?退一万步说,如果遇着囟球[①]说家儿,不考虑后果,把皇帝给说死了,那只好通过‘老包过阴’,‘还阳’或‘还魂’的办法解决了,不过有点麻烦,多绕点弯的不是。”
听着刘大江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不着边际,我几乎绕晕,惊讶、叹服之余,不禁调侃道:“刘先儿,说什么人的生死掌握在阎王爷手里,叫我看是掌握在你嘴里。你让谁死,谁不得不死;你让谁活,谁想死都死不成。阎王爷的生死判官不胜叫你来当,哈哈。”
入夜,我兴奋得睡不着觉。今天这场书,差点弄炸锅,幸好刘先儿及时救急,有惊无险,整体上还是取得了成功。谁说“福无双至”?这两天让人振奋,让人高兴的事儿就接二连三地赶到一块了。先是遇到了说书生涯中至关重要的“贵人”刘大江,让我在低迷中出现了转机,失望中擦出了希望之火花。进而诸多“第一次”的好事接踵而来:第一次领主弦儿,第一次成伙计份儿,第一次当“老师儿”,第一次说大书。而这四个“第一次”成就了我艺术人生的里程碑,极具划时代的意义啊。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有了第一次说大书的经验,在刘大江的鼓励和引导下,很快就有第二次、第三次、N次。每一次都是一种历练,练就胆量,练就处事不惊,随机应变的能力;每一次都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不足的弥补,从而不断地由生涩走向了成熟。越锻炼胆子就越大,渐渐地,无论这部大书是否听过,是否熟悉,都敢和刘大江一人一段轮替着说唱,逐渐形成了常态化。
不搁伙计不知道,一搁伙计吓一跳。刘大江虽然说书干得年数不多,喝墨水也不是太多,但肚子里装的东西还真丰富,会的书还真不少,且说出来的书都是我闻所未闻的。
包公案方面,除了已经介绍过的《宋仁宗私访陈州》之外,还有一部能吊起我胃口,听起来引人入胜,迫切想学的《移胎案》。
据刘大江介绍,《移胎案》系包公案里的一折,又叫《王文学告状》,也叫《肉头泥身子》告状,一个书目,三个名称。《王文学告状》并不为奇,包公案嘛,不是告状,就是喊冤的,奇就奇在肉头泥身子怎么告状?《移胎案》的“移胎”又是咋回事?
要不包公案怎么又被称为《包公奇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凡包公断过的案子总是千奇百怪,形形色色。无奇不成案,无奇不成书。《移胎案》一开头便发生了一件天大的奇事、荒唐事儿。老公公趁南学读书的儿子不在家,竟然摸到刚过门三个月的儿媳妇屋里,想发生点什么。结果啥也没发生,被儿媳妇撵了出来。按说这事儿就过去了,可老公公扒灰没扒成,却惹了一脸灰,害怕儿媳妇给儿子说,又害怕传出去,父入子房的事儿老丢人。就来个先下手为强,猪八戒倒搂一耙子,给儿子煽风点火。说儿媳妇与娘家哥哥王文学混而不清,被自己撞见了。儿子听风就是雨,不加思考,一怒之下,一封休书,就把媳妇王素英给休回娘家了。
事情越闹越大,娘家哥王文学听完妹妹哭诉,怒火中烧,掂起一口铡刀,到妹妹婆家门口去讨说法。老公公自知理亏,霸着儿子,闭门不出。王文学一怒之下,把他们父子告到太康县大堂。
事已至此,老公公只好豁出去了,买通了县官和半婆(专门检查妇女身体,类似于现在的女法医),硬无中生有,诬陷儿媳妇娶到家中三个月,已经怀孕五个月了。王素英百口莫辩,有冤无处诉,剖腹明节,屈死大堂。王文学含冤进京找包相爷告状。
知县吃了脏银,吐不出来了,就伙同手下衙役能干儿定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将后官宅已经怀孕五个月的官太太杀死,把胎孩儿移到王素英的腹中。此便是“移胎奇案”的由来。
至于后面的“肉头泥身子告状”更是离奇。官太太的头被小偷误盗,安在关帝庙泥胎周仓的身子上。王素英屈死的阴魂不散,附着在肉头泥身子上。然后这个肉头泥身子便会开口说话,被好心人李好善背到大堂上,找包相爷告状,几经曲折,终于真相大白,冤案昭雪,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这部书悲情连连,曲折离奇,引人入胜。和我后来听到段界平、王小岳、张怀生等名家演唱的《老包访太康》如出一辙,故事情节大同小异,略有出入。只不过后者剔除了肉头泥身子告状等涉嫌迷信和比较荒诞的情节。但我仍固执地认为还是我们的那个版本好,改新后的情节已经远远地不是那个味了。
以上两部书都是刘大江拾豫东艺人的书,然后又经过自己加工的。他有几部大书虽然我以前没听过,却是“在书”的,我亲眼看到了书本或手抄本。
比如他经常说的《洗衣计》,也叫《白秀英洗衣》《田二红开店》《张宝童试妻》,是收藏的,已经发黄、发烂的民国年间的鼓词古籍石印本。虽然刘大江是照着书说的,我听过几遍,但兴趣不大,没有在意看,也没有留神听,更没有学会。尽管有些词儿编得还有些文学性,比较文雅些,如有夫之妇白秀英定下洗衣计,勾引张宝童时的唱词就很精彩:“奴家虽然残花败,狂蜂浪蝶从未惊。甜蜜蜜的果子送与你,休要做假来撇清。”刘大江唱得朗朗上口,津津有味,导致我也记住了这几句。可是纵观全书,其情节结构和《儒林外史》差不多,从白秀英定下的“洗衣计”,到后来的“田二红开店”以及后面的“张宝童试妻”,“奇巧配”等故事,除了用主要人物张宝童这根主线贯穿始终外,前后并没有必然性的关联,可以彼此独立,造成了脱节。丝毫没有河洛大鼓长篇大书环套环,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觉得这部书跨度太大,不紧凑,太松散,不吸引人,所以我没学。
还有从清末木刻本《宣讲神义》中摘录出来加以改编的《沈布云中状元》,这是一个旧时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内容悲情缠绵,很是让人入迷。但我认为缺乏书筋调剂,没有笑料,大部分处于忧伤、沉闷之中,让人听得压抑,打不起精神来。刘大江善于深度挖掘,细化,但我觉得这部书他过于刻板“照书”,生搬硬套了,缺乏灵活,以至于情节活不起来,人物活不起来,唱书的活不起来,听书的更活不起来。所以不但我没学,就连故事情节到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最喜欢,最想学的,就是以后成为我的“看家书”的手抄本——《双锁柜》。《双锁柜》并没有见到原书,我所看到的是刘大江抄了厚厚的一个信纸本,夹在硬书夹中的。据刘大江说,他是抄刘山叉的,而刘山叉又是抄他的老师,五头张海谦的。张海谦的又出自何处,不得而知。总之,《双锁柜》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无缘欣赏张海谦、刘山叉的《双锁柜》,却对刘大江的精彩演绎非常看好。一边跟着学唱,一边毫不犹豫地把原书抄录下来,又揉进了我与刘大江的加工和创作,使其更加完美。然而辛辛苦苦整理的这部书,后来被王河清老师的徒弟王遂厚借去,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要了几次,说是弄丢了,好在当时已经烂熟于胸,不以为然。事隔多年,提起这事儿仍然耿耿于怀。不过这是以后的事儿了。
前面说过,说书分为“死口书”和“活口书”。比如俺老师王新章爱说“死口书”,书词和唱腔都是固定的,极少变动。而郭汉和王河清则擅说“活口书”,但和刘大江的“活口书”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不在一个层次。郭汉和王河清的“活口书”的“活”,仅局限于大框架不变的范围内,根据现场气氛适当的调整和取舍,临场发挥,对书词或唱腔做一些微小的变动,大方向不变。而刘大江的“活口书”可谓“大手笔”,“活”出了境界,“活”出了高度。他会冲破情节框架的束缚,大刀阔斧地砍削,纵横驰骋地添枝加叶,细如毫发的添油加醋。而这一切都是“现上骄,现缠脚”,“现打热卖”,临场发挥,常常在一念间,灵光一现,脱口而出,张嘴就来,容不得半点的思索和迟疑;而添出来的枝,加出来的叶却是非常合情合理,恰到好处,看不出半点嫁接或斧削的痕迹;而添出来的油,加出来的醋又是那么有滋有味儿,让人乐此不疲的品尝。很难想象,能如此轻车熟路,娴熟地驾驭长篇大书,把情节、语言玩弄于股掌之间,驰骋于说唱艺术之中的刘大江,才仅有四年多的艺龄!不得不另眼相看这个貌不惊人,却有着惊人本事的“高手”。
“活口书”闻之久矣,早在学艺之初,就听老师说及。请恕我井底之蛙,自学艺至今,刘大江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领教过的,把“活口书”活到极致的说书人。他真正地做到了让情节活起来,让人物活起来,让说书的活起来,让听众活起来。
有的笑了,你说得也太玄乎了吧?你说的让情节活起来,也不过是不拘泥于情节的条条框框而灵活多变;你说的让人物活起来,也不过是避免了千篇一律的脸谱化,刻板化,使人物千人千面,更加丰满、生动,性格更加鲜活,多姿多彩罢了。让说书的活起来,让听书的活起来,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书的和听书的都是死了不成。No,No,这里的“活”是灵活、活跃的意思。
这里所说的“活”,体现在说书的互动性。他突破了传统说书“一人一台戏”的模式,人物角色机动灵活,跳进跳出。一会儿是说书人,一会儿是书中人;一会儿是公子,一会儿是女子;一会儿是老公公,一会儿是老丈人;一会儿是老子,一会儿又装孙子……这不稀罕,因为说书自身就是一人多角的艺术,是需要连稀带稠一齐来,角色频繁置换的。重要的是他独特的互动方式:与拉弦的互动,甚至与听众互动。
与拉弦的互动,属于“对口书”的一种。说家儿与拉家儿对话、互动早在少时听说书就见过不少,俺老师和郭汉、王河清他们之间也经常说“对口”。在某种场合或情景下,拉家儿可以故意打断说家儿,进行插话、问话,谓之“插科打诨”,类似于相声的捧哏。如:
说家儿说:“哪位问了,今天说的是啥书?”拉家儿会接茬儿:“啥书啊?”“说的是……”此类对话有强调的作用。
说家儿唱:“要知来了哪一个——”拉家儿接问:“哪一个?”“来了千岁叫刘镛”……此类对话有助威,造势之作用。
说家儿唱:“说一个大姐整十七,四年不见整二十……”拉丝者打断:“说书的,你识数不识?十七加四等于二十一呀,你咋说等于二十哩?剩下那个一,你把它吃啦?”拉弦的接唱:“先说二十后说一,分两回说着俺省气力。”此类对话妙趣横生,可引起听众兴趣。
这类对话,可有可无。如果拉家儿不愿意插话或问话,说家儿就来一个自问自答也是可以的。王老师他们只是偶尔一用,并不经常用,即便用,也是事先约定好,怎样问,怎样答,以免出现差错,让人措手不及,闹出笑话。
这类对话,一般都是一答一问,一言半语,活跃一下书场气氛。一般不参与书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
和王老师他们的“对书”不同的是,刘大江在说唱中与拉弦的对话不仅是即时性、灵活性、甚至是强制性的。而且把拉弦的也拉到了故事里,扮演了书中人物的角色。
怎么叫强制性呢?像我吧,一般只要刘大江发问,要求对话,都会尽量配合,力争做到对答如流,合情合理。但在河洛大鼓行中,有不少不会说唱,专职拉弦的,俗称“单片子”。这些拉家儿大都不善言辞,不爱多说话,不然怎么学不会说书呢?这些拉家儿一般都是专心伴奏,不与说家儿掺和。说家儿呢,知道底细,一般不会向拉家儿发难,要求对答,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难堪和不快。刘大江则不然,你不会说逼着你说,不想对(话)逼着你对(话),赶鸭子上架,死蛤蟆也要给憋出尿来,直到逼得你开口为止。
像我们一块出来的“琴师”王矿子,性格不是一般的内向,不是一般地不爱说话。他奶奶说:“俺矿子在家一天说不上三句话。”在自己家中尚且如此,和我们出来说书就更不用提了,除了吃饭、吸烟必须要张嘴外,平时不是烟瘾大,怕饿死,恐怕连嘴都不想张,更不用说,说话还得动脑筋费气力哩。面对这样一个拉家儿,刘大江也不放过,还非要逼他开口对书不可。
我们在桃山大队的康圪瘩生产队说的书是《双锁柜》,开头有老财主余得水嫌贫爱富,假设灵棚昧亲的情节。既然假设灵棚,少不了买棺材,搭灵棚等事宜。
书说到这里,刘大江便成了余老员外,我和王矿子两个拉弦的便被指定充当了老员外家的长工。刘大江以老员外的身份向我们发话:“我说你们两个长工,这十钱银子你们拿着,到大街上棺材铺里给我买上一口棺材,快去!”
我赶紧伸手做从老员外手中接过银子状:“放心,员外,俺们这就去!”
王矿子如泥胎般地坐着,好像没听见一般,无动于衷。
刘大江转向了王矿子:“说你哩!去不去?”
虽然他是对着矿子说的,但矿子看不见呀,仍不答腔。刘大江急了,用鼓槌戳了戳矿子的胳膊,大声训道:“你眼看不见,耳朵也聋啦!问你话哩,是猪也会哼一声吧。”
都逼到这份上了,王矿子只得动了动身子,翻了翻白眼儿,慢吞吞,死气沉沉地应了一声:“中。”
为了活跃气氛,增强生动感、真实感和趣味感,让听众有亲临现场的参与感,刘大江可谓花样百出,在互动、对书方面,不但拿我和王矿子开涮,就连现场听书的观众也不放过,时常抓他们做“小夫”,来充当书中的人物角色。
河洛大鼓在农村的演出,称为“撂地”,大部分都没有舞台。说书人与听众仅一桌之隔,近距离接触,甚至说书人与听书人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刘大江利用与观众零距离的优势,和听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来获得“人气”。听书人亦说书人,听书人亦书中人。说书人、听书人、书场人、书中人融为一体,书中的人物置身于书场听众之间,书场的听众也“穿越”于书情之中。刘大江极善于把握听众心理,调动听众积极性,激发听众热情,唤起听众强烈共鸣。而且驾驭自然,得心应手,恰到好处,令人拍案叫绝。
刘大江说,根据经验和规律,距说书艺人最近的听众往往都是对河洛大鼓极感兴趣的书迷或铁杆儿“粉丝”。紧紧围绕在说书桌左右,紧紧地盯着说书人的脸和嘴,可笑的地方跟着笑,伤悲的地方跟着难过,紧张的时候瞪着眼张着嘴的,大都是年轻小伙和小学生娃们。他们听书热情高,异常活跃。说书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动着他们的心。如果和他们互动,对话,一般都会非常乐意地配合,参与其中。
还拿《双锁柜》说事儿。假设灵棚统复杂哩,得动用好多人啊:得有人买棺材,有人搭灵棚,有人打墓,有人报丧等等。这么多事儿,这么多人,显然刘大江一人忙不过来,拿我们拉弦的垫背也不够呀。于是,说书的,拉弦的,听众都成了余老员外家的家郞、院公、长工和帮忙的。刘大江是办事儿的,或是长工头,给我们分派任务:
指着我和矿子:“张三、李四,你俩到大街去买棺材!”
我们赶紧响应:“是!”
指着说书桌左右站着的四个小学生:“郭五、马六、冯七、赵八,你们四个还站这干啥?还不快去天井院里搭灵棚!去不去?”
四个学生听说派下任务,高兴坏了,像回答过老师提问一样,一齐起哄:“去!”引得现场鼓掌喝彩,气氛热闹非常。
有个学生没有被点名,派任务,感觉受到冷落,有点不满意,主动请战:“咋没有我的活儿哩?”
刘大江顺水推舟,就把员外家中一个最小的家郞叫来兴的角色,安排到这个学生身上:“来兴,你小哩,出力活儿干不动,给你找点轻活干干,去王家寨报丧去吧?”“来兴”一听,高兴得手足舞蹈,连声答应。
围在书桌前的一群小学生,为能配合书中人的角色而倍感自豪,积极性特高,甚至顾不上去厕所尿尿,硬憋着,唯恐失去了展现自我的表演机会。
当然,如此地放开,大胆地与观众融为一体,携手合作,共同演绎说书艺术的“活”,并非一帆风顺的,有时也有失败的风险,这就需要说书人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由于事先并没有约定和串通好,听众对这突如其来的发问会产生三种可能性。这时说书人就会随机应变,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一是对方无应答,就会再追问,直至回答为至,如果这位听众特别熟悉的话,也可以自嘲:问着聋子或哑巴啦,再问别人吧。注意,必须是知根知底,摸透脾气的才敢这样说,否则可能引起反感和难堪。二是如果对方回答:“去”或“是”等同意的话,就完全符合书情,达到了理想的效果。三是如果回答:“不去”或“不行”等不同意的话,只好退而求其次:“你不去(不愿意)算啦,我再找别人。”就转向另一个听众重复以上过程。
桃山、康圪瘩结束之后,我们下田山说(书)了几天,然后又折回至坡池大队,一来二去,一个多月了,本来正说好书,干好生意哩。刘大江却和我商量要回家一趟。原因有两点儿:
一是河南人,尤其是豫西河洛一带,大多数都“恋家”,不像四川、江、浙一带,讲究大丈夫四海为家,志在四方,出远门几年不回家习以为常。刘大江家中事儿多,出门不长时间,就要回家看看,转转,安排一下才能再次出来。
二是黄河北说书虽然书好说,生意稠,但由于经济落后的原因吧,书价上不去,人们还好“搞价”,尽量少掏钱。说书是按人头儿算的,按当时的行情,每人每场两块钱,三个人就是六块。搁黄河南的行情,大多数地方三个人六块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很少有人讲价钱。到黄河北就不行了,好多地方都嫌钱多,把书价往死里压。三个人六块钱根本办不到,至多拿五块钱,甚至再压一下,只能拿四块。这样下来,说书三个人只能得两个人的工资,把一个人挤没有了。一句话,黄河北说书不兴“大班口”,人多价钱上不去。经济效益低,还影响说书生意。鉴于此,说书要想在河北生存,最多只适应两个人,我们三个人必须裁员。裁谁呢?自然而然就是矿子。
刘大江没认识我之前,还指望矿子给他拉弦呢。但我们搭班后,他唱我拉,我唱他拉,矿子的弦儿基本用不上了,成了可有可无的多余人物,陡增了我们的负担。就算我们有爱心,情愿照顾他,背这个包袱,可河北不允许三个人说书啊。刘大江的意思是,他把人领出来了,如果是好好的人,直接打发走了事。但矿子是失目的残疾人,不能撂在半路不管,这不是人办的事儿。借这次回家的机会,我们的“三人行”告一段落,把矿子送到家里,交到奶奶手上,才算尽到了责任和义务。然后重打鼓,另开章,重返河北,整装再战。
其实人家刘大江早计划好了,说是跟我商量,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即使反对也无效。况且人家说得有道理,为啥要反对?再说一个多月了,我也有点想家了,回家转一趟未尝不可嘛。
有的说啦,人家回家看看,是看老婆哩。你没媳妇,想的哪门子家?瞧你说的,没媳妇就不能想家啦?穷家难舍,何况家中还有老娘?说不定打了一个喷嚏,老娘正在家中念叨我呢。
那就回呗,还犹豫个啥?
[①] 囟球:河洛方言,同“欣球”,指缺心眼的憨傻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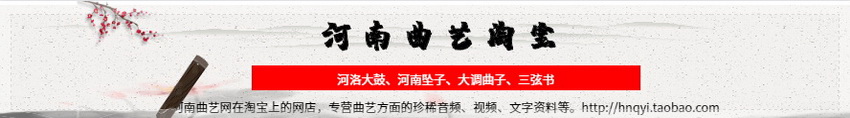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