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三十八

时间从指缝中悄然滑走,三天还愿书不知不觉就结束了。一切顺风顺水,神满意,人高兴,皆大欢喜。送神交号烧纸箔时,风吹纸灰儿满天飞。凡烧香敬神的善男信女们都懂:纸灰起得越高,神越满意,“愿”领得越痛快;反之,纸灰不起,沉落在地,说明还有没愿意到的地方,神有意见,闹别扭。这次纸灰都快飘到半空了,神婆们看在眼里,乐在心上,纷纷交头接耳:“咦,看五龙爷这回真满意,高高兴兴听书,欢欢喜喜领愿。多好!”
神满意了,人却意犹未尽。听书人不满意,三天书正听到吃劲儿的地方,弄得不上不下的,心里膈应得慌;说书人不满意,短短的三天,人才刚刚混熟,屁股才刚刚暖热,就要卷铺盖离庙了,有点恋恋不舍。听书人还想听,唱书人还想唱;说书人不想走,听书人又想留。咋办?往下继续?
交罢号,趁人还没散去,王小伟不失时机地趁热打铁,掏出了死缠烂打的本事,和老头搁兑[①]起来:“爷儿们,咋弄?不中再续几天?”
经小伟挑起个头,大家便纷纷附和:“就是,来一回说书的不容易,黑叔,再说几天,都还没听过瘾哩。”
通过这两天打交道,才从别人嘴里知道这个老头叫黑子,小娃儿们一般喊黑爷,成年人大多喊黑叔。被唤黑叔的老头不慌不忙地从烟布袋里搲上一锅旱烟沫,慢吞吞地掏出打火机点着,吱吱吸了两口,这才拿白眼儿扫视了一下众人,缓缓地说:“都想听(说书),钱从哪里起?”
众人一时被噎住,是呀,钱是硬门事儿。有钱能办趁意事儿,无钱寸步难行,没有钱拿啥打发说书的?
有人提议:“寻猴子去。他是队长,叫队里照头说几天。”从话里听出来,他们说的猴子是人名,可能是前坡队的队长吧。
有人调侃:“就这吧,寻孙悟空也不管用。猴子急得跟猴样儿,队里的上交款都收不上来,还有心事管说书这事儿?寻也是白寻。”
“都别说啦!”正当大伙七言八语乱哄哄时,老头把烟袋锅儿往透风鞋(凉鞋)底子上一磕,吐一口痰,用脚一趋,又翻了两下白眼,吐出两个字,“兑钱。”
我观察老头的白眼儿可不是随便翻的,每翻一下白眼就有新的想法,每翻一下就有与众不同的见解,每翻一下就是一个主意。现在我有点欣赏老头的白眼儿了,看起来那么顺眼儿,舒服,那么可敬可爱哈。
果不其然,立即响起大多数附和声:“中!”但也有人提出疑虑:“兑钱?能收得起来吗?首先我没啥说,兑多少钱儿也心甘情愿地掏,可敢保证所有人都能拿得出来?咱这地儿,没钱家儿太多,有钱儿人老少。好多家儿吃盐舀油的钱都愁,让他们兑钱说书,中不中?还有家儿听说书跑得可快,叫掏腰包,好比割他身上的肉,把拴到裤腰带上,死活都不肯往外出,铁公鸡一毛不拔。遇着这号人,能拿他有啥办法?万一钱收不起,照头人可是坐萝卜[②]的事儿啊,咋收场哩。”
这确实是个事儿,谁也不敢担保百分之百能把钱收上来。大家一时沉默,老头又接着抽起了烟。
刚说罢书,口干舌燥的,本不想多说话,见陷入僵局,便喝一口热茶,清了清嗓子,满怀歉意地说:“让这么多老少爷们为这事作难,俺也觉得可不好意思。能再说几天(书)更好,实在不行也不要紧,生意不成情义在嘛。”嘴上说着这样客气的挂面子话,心里却有所不甘,忍不住又转了话头,“不过,兑钱说书的话,不如收粮食。咱农村人最缺的是钱,最不欠的是粮食。如果一户兑块把钱说书,恐怕好多家儿拿不出来,即便能拿得出来,也心疼哩慌。粮食是咱自家地里长出来的,不算缺欠,刚收罢麦,哪一家不是缸满囤流?谁家拿不出几斤麦来?出两瓢粮食不值个驴价马价的,好多家都不会在乎。所以说,收粮食比收钱要容易得多。”
这一说,大家纷纷点头,觉得这倒是个好办法。老头又朝我翻了翻白眼儿:“粮食倒是好收,可你说书的是要钱呀!总不能说罢书,给你俩弄两布袋麦子背着东南西北地跑,像话不像?”
众人哄笑,我尴尬地跟着笑,赶紧连摇头带摆手:“俺是说书的,又不是地主收租子的,背着粮食跑来跑去的算咋回事哩?再说俺说书的手无缚鸡之力,拉弦的一个轱辘还是没气,哪能背得动沉腾腾的一袋粮食?把粮食粜出去,不是变成钱了?”
老头白眼儿一翻,把烟袋锅狠狠一磕,当即拍板定音:“算是!明早我就收粮食。”
有的说,你咋会想出这古董门儿[③],说书收粮食?其实咱只是个书呆子,光会说书,哪懂得做生意的门道儿?收粮食说书的主意,并不是我能想出来的,既非首例,亦非独创,而是前辈们已经开辟过这条路,探索成功的经验。我不过是走前人走过的路,吃前人嚼过的馍,比葫芦画瓢地借鉴、照搬罢了。
其实早在学徒时,就听俺老师说过,最早的时候,据说说书也有不要钱,要粮食的,说一场书能收一石麦哩。按通常的说法,一石120斤,就按一百斤麦算,折合成钱,搁过去是不是极高的工资啊?看起来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创说书收粮食的先河啦。
解放前不是大集体化,说书当然也没有生产队或大队包场[④]的所谓“官书[⑤]”或“闲书[⑥]”之说。河洛大鼓的包场主要用于大户人家的“唱堂会”和一般人家的“还愿书”。有人可能不知道堂会是咋回事儿,是指旧时豪绅官宦等大户人家或有钱有势的财主权贵,因添丁、祝寿、升迁、宴宾、贺喜、祈福等事由,在自己家中举办的隆重演出活动。因多在厅堂之上,故曰“堂会”。唱戏的称为“唱堂会”“堂会戏”,说书的也称“唱堂会”或“说堂会书”。能受邀登堂入室,说堂会书的都是金字塔上的顶尖人物,说书行里的佼佼者,是大干家儿,名说家儿,一般水平的艺人根本轮不上,挨不着。据说民国二十五年,蒋介石的五十大寿在黄埔军校洛阳分校举办,河洛大鼓的祖师爷,第一代艺人吕禄还应邀参会,演出助兴呢。
堂会书、愿书之类的包场,都是冷热活儿,不可能天天有,不可能人人分到这杯羹,不足以形成职业,难以养家糊口。说书要想生存,单靠唱堂会、还愿来维持生计肯定不行,于是,“撂地儿”和“唱棚书”也是过去的主要行艺方式。
所谓“撂地儿”,也称“撂明地儿”“摆地摊儿”。就是艺人临时在庙会、集市、街中人多热闹的地方拉开摊子,打开场面说书。长期固定场所的比较讲究,有用于遮风挡雨的简易布棚,备有桌椅板凳之类的,也可称为“书棚”。短期或临时的说书没有棚子,仅一桌一椅,听众或立或坐,团而围之,也称“露天书场”。
唱棚书又称“坐窝儿”“占园子”“蹲穴”“棚下书”,因最早在书棚里唱,故得名。后来发展成茶社、曲艺厅、小剧场等相对高档的固定场所行艺,也称“坐桩生意”或“坐摊儿”。唱棚书多在城市,人多,听众资源广,且说书人艺高,书多,才能经年累月地站得住脚,有饭吃。
无论撂地儿,还是坐棚,以至后来的曲艺厅、曲艺茶座,说书人的报酬从哪里来?汗得从病人身上出,说书钱还得从听众中间来。把听众的钱汇集到一起,就成为说书人的书资。有人出头把钱收上来说书的叫“收钱”,大家主动掏腰包,把钱凑齐说书的称为“兑钱”。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大鼓传承人陆四辈介绍他的老师,河洛大鼓第二代艺人张天倍撂地儿说书收钱的盛况:“偃师有一个老车站,门口就有一个艺人们专门撂明地的演出场所,就是收钱的。说半个钟头,或者二十分钟停下来,开始收钱,手里端着茶盒,或是铝钵,嘴里说着奉承话儿‘没君子不养艺人’‘金胳膊银手,越掏越有’……挨个地转,听众大部分都往里丢钱……过去听家儿多,俺老师父他收钱一回多得很……”
陆四辈先生说的是河洛大鼓最早的收钱方式之一,是说书人自己向听众收钱,类似于讨要的性质。还有的行艺者只管专心说书,收钱的事交由当地有威望,有号召力,有责任心,且有一副乐于助人之热心肠的“牌官儿[⑦]”来胜任。后来的曲艺厅、曲艺茶座等场所改为售票,实际上是收钱功能的升级和完善。
撂明地儿、占园子等坐桩生意多适应城镇人流量大的地方,而令河洛大鼓大有作为的,最大的市场却是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在都市站住脚混得下去的说书人屈指可数,绝大部分活跃于山村田野。在那个没有大集体,没有生产队包场说书的年代,游走在乡村的艺人是怎么生存呢?城里说书收粮食是不现实的,他们吃的还是拿钱买,哪来的粮食?而农村恰恰相反,要钱没有,要粮食嘛,还可以考虑。于是,很早以前,就有了农村说书收粮食的行艺方式。
听俺老师说,在过去说书收粮食有几种收法:刚到一个生地方,找不到合适“牌官儿”承头来收粮食的话,说书人就自力更生。说罢一场书后,说书人自己拿着布袋,挨家挨户地收。一般人家都给,个别不给也没事儿。收得好的话,都比包场说书强。还有一种是说书的拿着布袋,逐门逐户地唱,说上一段儿,主家便搲上一瓢麦(或玉秫秫),一天下来,收入也相当可观。不过这种方式有点类似于卖唱乞讨的性质,这也是说书人被称为“巧要饭儿”的由来。不过乞讨卖唱似乎是莲花落的强项,河洛大鼓艺人常常以说书先生自居,很少有放下身段,向人开口讨要的。
这都是旧社会的事啦。解放后,走集体化道路,党和政府介入,说书也有了高雅的归属——曲艺。艺人成了演员,身份地位改变,行艺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搁明地儿,乞讨卖唱等陈规陋习被逐步淘汰或取缔。农村说书挨门收粮食的做法被大集体生产队包场所取代,从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传说。
谁曾想到,世事如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后,土地又包产到户,从大集体又回到了单干,生产队改头换面成了片、组,成了空壳儿,给农村大集体包场说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穷途末路之时,穷则思变。说书人不得不探索各种生路,于是,收粮食说书又死灰复燃,逐渐地有所抬头了。
刚学徒时,老师就有收粮食的打算,却一直没有付诸行动。一来当时生产队说书还勉强凑合,并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想去开辟这条生路。二来说书收粮食并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儿,困难重重。首先得抹下面子,放下架子,脸皮不能太薄,得学厚点,能看脸色,能吃话头儿。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可能人人都不给你甩脸子。再者怕麻烦,怕费事,弄不成事儿。粮食得一碗一碗地收起来,积少成多,再想办法卖掉变成钱儿。说书人既得说好书,还要操其他很多闲心,顾住这头,顾不住那头,远没有包场说书轻松自在。三来我这人脸热,不会花言巧语,不会看眼色行事儿,放不下说书先生自命清高的所谓面子,上门收粮食一点儿都不粘闲,加上领两个失目人拖累,哪还顾得上?
自学徒到出师,我没有亲自收过粮食,却经历了不至一次。当初领大书走山沃,经过石井的许庄时说过的那场书,就是一个热心的老头儿——“牌官儿”出头给我们收的小麦,说一场书绰绰有余呢。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收粮食说书,此后和王河清老师搭班时,在别人的帮助下,收过几次玉米,也是比较成功的。有过以往的经验,所以才有龙潭沟说书收粮食的主意。
书理表尽,兜了一大圈子又绕了回来。老头办事雷厉风行,次日一早,叫上两个年轻人,就张罗着收粮食,还让我在后边跟着。本不想同乡亲们面对面地难堪,但老头自有人家的道理:一是有我同行,可以行使监督权,以示公开透明,以免落下吃利打拐的嫌疑;二是当着说书人收粮食,好多人家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拒绝,会收得多一些,顺当一些。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人家替咱出力、跑腿、办事儿,总不能想吃肉又害怕腥嘴吧?只好硬着头皮,涎着脸尾随在他们的后面。
实践证明,这个老头不仅是称职的好“神头”,更是个不折不扣的好“牌官儿”。发现他很有些长辈的威严和凛然正气,说话办事儿非常硬扎,说一不二,几乎没人敢犯犟。所到之处,纷纷慷慨解囊。布袋倒进一瓢一瓢的麦粒儿,在哗啦啦源源不断地升高。当然,也有例外,有极个别年轻人不买账,嘻皮笑脸地喊着黑叔,却说:“俺不听说书,也不兑粮食。”老头毫不含糊,把白眼儿一翻,霸气地怼了回去:“不听说书也得拿粮食!咋,你不是咱村人?大家群儿,小家轮儿。人家都拿啦,你能尿到圈外边儿,老特殊?不拿,中!以后你家有啥事儿可没人管啊!”一番话,对方乖乖地出粮食。不得不服气,老头的钳子硬,能拿捏住事儿。
老头不仅在前坡收到了一百多斤麦,宽宽绰绰地续了五天书,还跑前跑后地四下张罗,帮我们“写活儿”,如法炮制,在北洼、后旮旯、驼腰等几个小队,稳稳地扎住了书场,说了十多天书。最让我记忆尤深,难以忘怀的是张沟村的队长张秉。
张沟藏在龙潭沟北面的大山深处,从前坡到张沟须翻一座不算太小的山岭。说书人的到来,四十多岁的队长张秉一见如故,非常热情地招待。他只安排说书,却闭口不提收粮食的事儿,让我们十分纳闷。初见面拘束,不便多问,熟识了,就开始试探:“老哥,说书队里有钱吗?”
张秉哈哈地笑着:“老弟,现在生产队啥样儿你还不清楚?有屁钱!”
我疑惑:“那说书……”后半截话没说出来,意思很清楚:你没钱还不收粮食,说罢书俺们的工钱从哪出呢?
队长岂能听不出我的话音?就爽朗地说:“一家一户收粮食太麻烦。老弟只管心装到肚子里说你的书,到时候工资少不了你一个纸角儿。”接着说出了他的打算:现在干嘛要费事儿,下去一户一户地收麦?能收得起不能还是另回事儿。不如自己先想办法把钱垫出来 ,等以后分摊到公购粮或上交款上,每户多收点钱粮不就行啦?反正多收的也没贪污,取之于民,用不于民,有何不可呢?比起单独收粮食来说,人家这个办法要技高一筹啊。
按理说,说书的到哪吃啥喝啥,就凭队长一句话。说(书)不说,说几天(书),都是队长说了算。说书的到哪都得和队长搞好关系,一般都得点头哈腰,极尽所能地阿谀奉承,甚至还有的低三下四,一路小踮脚地帮队长干这干那的。咱手懒嘴笨,还没眼色,不会甜言蜜语,叔长哥短地称呼。那种见啥人说啥话的江湖套路一辈子也学不来。不过这个张秉队长根本用不着我们的示好和巴结,反倒给予了体贴入微的照顾和帮助,加上张秉嫂子纯朴厚道,把我们当成亲人般的待客之道,给人一种宾至如归之感。我叫他队长反觉得生分、别扭,于是就直呼“秉哥”。
张沟说书的几天里,秉哥放下手头上的许多活儿,专门在家陪我们。晚上说书,早上睡醒了没事儿,秉哥说:“老弟,在家里着急,烦闷,我领你们山上到处看看吧?”太好啦!我们欢呼雀跃,求之不得哈。
山里的盛夏本身就没有平原的酷热,加之清晨气温较低,又吹着微微的凉爽的风,真个是轻松愉快。秉哥既是向导,也是导游。我们丝毫不担心山里迷失了路,摸不回来。

“那是小皇姑庵,那是大皇姑庵……” 秉哥带领我们沿山腰缓缓西行,一边走,一边指点着前面不远处,郁郁葱葱掩映中,崖头下的两处石厈向我们介绍。
“皇姑庵?是皇姑住的地方?”我们满腹疑问,哪一个皇姑脑子里进水啦,发什么神经,跟到这深山后背,穷山恶水,鸟不拉屎的地方,钻到这石崖下居住?
秉哥看出了我们的困惑,嘿嘿一笑,道出了一段委婉凄美的爱情传说:
听老年人说,这事儿出在东汉末年,当时宦官乱政,董卓专权,朝廷内祸事不断。说不清是哪一年的哪一位皇姑,有的说是逼婚,有的说是遭人陷害,就逃出洛阳的深宫内院。护送她出逃的是一个宫廷的小银匠和一个马车夫。原打算去山西绛州避难的,马车沿新安北山通往山西的古道一路狂奔,进了青河川,走到红崖寺前的岔道口,就听到后面追杀声越来越近。情急之中,马车夫想出一条让皇姑脱身之计,让小银匠扶皇姑下车走另外一条道,顺着荒凉的龙潭沟逃进深山。自己却驾着马车顺山沃河川古道,直奔黄河岸边,驱车跳进波浪涛里。当追兵赶到,见河面漂着一辆宫车,料皇姑已赴河殉难,就拨转马头回洛阳复命去了。再说皇姑成功避过一劫,和小银匠逃进了龙潭沟。当地人很同情皇姑的遭遇,就统一口径,来一个瞒天过海,把皇姑隐藏了起来。不敢在村里住,害怕人多嘴杂,走漏风声,就领他们到村后不远的一个石厈里躲了起来。后来又怕被人发现,就把皇姑单独转移到离村较远,更隐蔽的一个石厈。久而久之,前面离得较近的石厈人们称为“小皇姑庵”,后面离得较远,较隐蔽的叫“大皇姑庵”,因前面的小皇姑庵后来小银匠长期居住,故也叫“银匠庵”。
听秉哥讲故事,我们为马车夫的壮举而唏嘘不已,同时也为这穷乡僻壤能引来公主而羡慕不已。常听说“穷山沟飞出金凤凰”,殊不知龙潭沟也能招来皇公主哈。但也半信半疑:“哈哈,秉哥,这不过传说罢了。哪有公主会躲到这个地方,要较起真来,恐怕背着干粮也打听不上吧?”
秉哥一脸认真:“不用笑,也不用背着干粮打听,我叫你俩马上相信。你往龙潭东面看——”
我们转了个方向,看向龙潭以东,距骆村不远的河南岸,五龙庙东侧有几户人家。“不就是几户人家嘛,有啥看?”
“那里原来有个接官厅,现在看不到了。”秉哥又接续了上面的故事:
多年以后,洛阳政局渐趋平稳,皇上历经周折,多方打听,终于得知皇姑在龙潭沟栖身,就命大臣来迎接她回宫。皇姑自隐居在龙潭沟,得到纯朴善良的乡亲们悉心照顾,生活虽无法与宫廷相比,却也衣食无忧。此时的皇姑已经和当地村民水乳交融,习惯了布衣素食和幽静山水,产生了深深的情感和依恋,再也不愿回到勾心斗角,血腥不断的皇宫内院。听说皇上派近臣来接,她和乡亲们一起商量,把村头一家较宽敞的房子做了临时的“接官厅”。皇姑在接官厅举行了接见仪式,表明了坚不回宫的心志。特使无奈,只好回京复命。
后来,皇姑和小银匠患难之中,日久生情,最终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在这朴实简陋的山洞里自食其力,安然度日,偕老百年,成就了千载流传的美丽佳话……
秉哥说完了,我们却沉浸其中,久久不能自拔。尤其是小伟,当时还没有媳妇,听说皇姑跟着小银匠,可眼气[⑧]坏了:“唉,小银匠真是艳福不浅,娶了个公主当老婆!咱咋没这好命哩?啥时候能交个桃花运,别说公主啦,只要是个女的,会两条腿走路都中啊。”
谈笑风生之间,我指着龙潭北面的半山凹里,几乎被树木杂草淹没,荒凉萧条,破败不堪的一座房子问秉哥:“那一家儿远离村庄,孤零零地住在山脚下,出门又不方便,图啥哩,咋不搬到村里住呢?”
秉哥说:“哎,你可别小看这一户人家,大有来头呢。虽只有一户,也是一个村子,这个村叫‘骆家’。你听说骆村恁大,人恁多,有姓骆的没有?没有吧。这里住的却是正而八经的骆姓人家,是名副其实的‘骆家’。 不仅如此,还不是普通的骆姓,是骆宾王的后人呢。”
“骆宾王是谁?”王小伟插问。
“瞎家伙。”为了显摆自己有文化,有知识,不等秉哥回答,我就抢先一步嘲笑小伟,“连骆宾王是谁都不知道?唐初四杰之一,可出名啦。你要还不清楚,那首‘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你学过没,那就是骆宾王的诗啊。”
前面第十三章里,望古垛说书的情节提及过骆宾王。和上面提到的皇姑的经历差不多,骆宾王也是遭武则天当局追杀,一路逃出洛阳,途经北冶的王坡遭遇山洪暴发,眼睁睁地望着洪水无情地把自己的小儿子吞噬、冲走,才有了“望古垛”这个地名。一直快到北冶,河水把孩子滩了出来,才有了“滩子沟”的地名。骆宾王含泪把孩子埋在望古垛对面的岭头,又有了“舍坡头”(石坡头)的地名。父子之情难以割舍,就在埋葬儿子附近的岭上住下,于是骆宾王住过的村庄就叫现在的“骆岭”。后来所说骆宾王落脚到漏明崖了,那里留下诸多他题写的诗句和生活过的遗迹。
很多人认为骆宾王晚年是生活在漏明崖的,凭据是那里有一个现在仍存的“宾王洞”,传说就是骆宾王生活过的地方。另外还有他著名的《漏明吟》佐证:“渑邑漏明呈奇景,悬崖万仞石棱曾;唇山白雾共旋绕,河水波绿萦带风。”
骆宾王在漏明生活得好好的,怎么又跑到龙潭沟了,而且还有后人?今天这是头一次听说,将信将疑,倍感稀奇。但秉哥说的证据更确凿,更可信:你说骆宾王在骆岭住过,骆岭有一家儿姓骆的吗?没有吧。在漏明有没有骆姓的?也没有吧。骆岭、骆沟、骆村,只能说明骆宾王路过或生活过那些地方而已。可这个骆家就不一样了啊,人家世世代代都姓骆,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是正宗的骆宾王后代。为啥不肯搬出来住,就是要苦守祖根啊。更重要的是,人家还能说出埋葬自己祖宗骆宾王坟墓的位置在哪,你能不信?
秉哥说得神乎其神,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不禁暗自庆幸:原来还嫌龙潭沟穷,说书榨不出啥油水,没啥吸引人的地方,犹豫着不想来呢。幸亏是下决心来了,不然将错过结识那个老头,叫黑子的“牌官儿”,还有秉哥这样绝好的队长啊,还将错过龙潭沟这二十多天的书,更可惜的是,将错过皇姑庵和骆宾王的美丽传说啊。
就这还不算,只是开了个头,秉哥本来是打算领我们看“一线天”和“刀碑石”的,还未到正经地方呢,就已经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只是开了个头,好戏还在后头呢。
龙潭沟有魅力,有故事,有厚度,足以吊起我的胃口,吸引我更加地深入。龙潭沟,不虚此行!
[①] 搁兑:河洛方言,这里有“商量、说合”的意思。
[②] 坐萝卜:河南方言,“作难、不好过”之意。
[③] 古董门儿:河洛方言。古董,此处指非正常,或不合常理的人和事儿。门儿,此处引申为门路、门道、窍门儿。古董门儿,即超乎寻常的想法或不按常规出牌的奇招、怪招。
[④] 包场:由某人、某村、某单位包揽说书的食宿、书资等所有费用,艺人无须另外收钱,称之为“包场”。
[⑤] 官书:所谓“官书”,就是集体(生产队或大队,厂矿或单位等)出资,听众人人都有份儿的书。也指官府介绍、安排的书。详见《河洛大鼓志》。
[⑥] 闲书:没有任何事由(请神、还愿、开业庆典、祭奠等活动),纯属休闲娱乐,图个高兴的说书称为“闲书”。详见《河洛大鼓志》。
[⑦] 牌官儿:河洛方言,听音记字。不是干部,却在村里爱出头,能管事儿,能号召力的人,也叫“排官儿”“派管儿”。
[⑧] 眼气:新安一带的方言土地语,“羡慕”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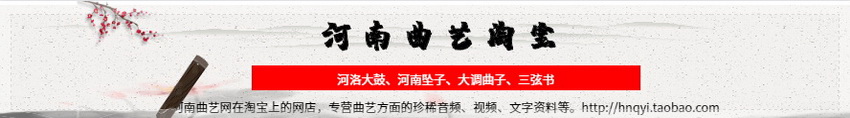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