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四十二
三走龙潭沟,高银虎基本上是被我生拉硬拽去的。
同高银虎搁伙计,可没有与王小伟的齐心协力,也没有王小伟随和、言听计从。说起前山说书不行,奔赴后山龙潭沟时,银虎就有点不乐意:“钻进老后山旮旯(方言音读gēláo),有球啥出息!能有书说吗?”当我把皇姑庵,刀碑石等景致和传说吹得天花乱坠,又历数龙潭沟人如何如何地厚道,纯朴时,他才有点动心,勉强地答应下来。
我们在崔沟老官岭说的最后一天书,不能再折回去走大路,那样太绕远。就抄了近路,直接由老官岭向西,下去山就是漏明河,出去到前口,从青河川一直往西即到龙潭沟。这样截近了十几里路,省去了不少时间,但近是近了,路却难走了许多。山势太陡峭,下山的羊肠小道荆棘丛生,碎石交错,行走困难。走过山路的都知道,有名的“上坡不美,下坡蹿腿”,我一个明眼人倒不觉得啥,可把高银虎这个“一盏灯”难为得不轻。
高银虎常自嘲:两个灯泡,一个钨丝闪了,剩下的一个还是残次品。那一只独眼睁得怪大,看东西却是模糊得很。大字能识上三五个,可是把字儿塞到他眼里也看不清是啥。再熟识的人,头碰头,面对面,不搭腔说话,永远无法辨认是谁。说他的一只眼不管用吧,多少通点路儿,能分清白天夜间,抬头看天,能看到太阳在什么位置。走宽路、平路,照着那一角子,马马虎虎凑合;走山路,上下坡,高一下,低一下,深一脚,浅一脚,可真是够呛了。要是没人照顾,简直就是寸步难行哈。
如果单是空人行路倒还将就,问题是我们的行李也特别累赘,除了演出工具弦子、鼓板及必要的行囊外,陡增了一个音箱,一个高音喇叭和一台扩音器。这些东西既笨重又娇贵,死沉死沉的,携带不便,还不经摔碰磕打。我尽量挑重的、大的,不耐磕碰的拿,尽力能多拿就不少拿,实在拿不住的才只好让银虎分担一两件。弦子、音箱、扩音器太脆弱,让他带着不放心,只有我拿,分给他一个提包和一个高音喇叭。提包装的是衣服,随便摔打没事儿,高音喇叭这玩艺儿也结实,一般磕碰不坏的。
到老后山沿去,高银虎本身心里就不太情愿,又摊上窄、陡、滑、磕绊的山路,气就不打一处来。一边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走路,一边牢骚满腹地嘟囔:“听着你的上悫山不用问路[①],早知道路难走成这,受这种罪,说啥我也不去龙潭沟那鬼地方!”
我也有点理亏,不该贪图节省路程和时间,没考虑到高银虎眼睛不好使,行走困难,可已经下到半山,再返回去不可能了。现在弄成这缸醋了,他怪上几句也情有可原,不能计较。于是赔着笑提醒:“都走到半路了,说这还有啥用?专心走你的路,小心脚下。”
说着小心脚下,已经来不及,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高银虎脚下一滑,身子一趔趄,屁股狠狠地蹾了下去,喇叭已经从手中飞脱,先是“哐当”一声掉在乱石堆上,进而“骨碌碌碌……”顺山坡滚下。我心中一沉:完啦,这个喇叭要报销了。所幸的是,没滚多远,就被一丛荆棘卡住。要是滚到沟底,别说喇叭,恐怕连个喇叭零件也难找到。
顾不上喇叭好坏,先看看人摔啥样,毕竟东西没有人重要哈。赶紧把银虎扶起来,忙不迭地拍打着身上的灰土和草屑儿,关切地问:“啥样儿?”
对我的好意,高银虎不领情,不买账,这一跌摔疼他不说,摔坏了喇叭更心疼得圪撩乱蹦,显然把火儿彻底给摔了出来了。本来就很大的独眼儿瞪得溜圆,似乎冒着火星,越发大得吓人。脸上怒气不息,双脚一蹦大高,像牛犊似趵起了蹄子,撒起了欢儿:“东西毁完啦!要去你去,我不去!走,回家!”
先前的两次埋怨我都忍了,可“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一忍再忍,再再忍就不想忍了。搁伙计得忍让、包容,但并不代表得一味地宠着,哄着,到时候惯到头顶上拨拉不下来了。忍让并不代表软柿子好捏,好欺负,怕你,任由你强横。我往下紧走几步,从荆棘丛里取回喇叭,还有音箱、扩音器、弦子重重地往他脸前一放,话头有点不好听,语气也很强硬:“给,东西给你!你走吧,我一个人去!”然后头也不回,气冲冲地快步下山。
这回该轮到高银虎没脾气了,愣在了原地,洋鬼子看戏,傻了脸啦。把他撂在了半山腰,上不来下不去的。以他的视力,没人帮忙给他充当路标和向导,将是寸步难行。有本事蹦呗!蹦到天上也没人拉你。
高银虎不愧是高银虎,能大能小,能软能硬,一张面孔变得比川剧的“变脸儿”还快。刚才还是怒容满面,怪羔似的,一转眼就喜笑颜开,朝我喊道:“囟球,你真打算把我撇到这半山里嘞?”
我回过头,仍然是冰冷的语气:“你不是不想去嘛?我也不能把你硬背去,强扭的瓜不甜!”
“说句笑话,你可当真啦。去,去,去,哪能不去?”高银虎忙不迭,一连声地回答。
“打算去赶快走!”我折回,重新拿起了行李。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说啥“银虎”哩,分明就是纸老虎,外强中干,欺软怕硬哈。跟他说好话,他越摇头摆尾耍威风;我硬起来,他就立马松不唧地萎了下来,软得一塌糊涂。武松能打真虎,就不信俺武成治不了你个银虎哈!
银虎这次服帖了不少,老老实实地背起行李,规规矩矩地跟我下山,再没有了牢骚和怨言。哎,早知如此,这一跤应该早点摔哈。
银虎不怪了,安生了,经过这番折腾我的情绪却消沉起来。不禁联想到河洛大鼓,这两年何尝走的不是类似这样的下坡路?而且一路下滑,很陡,很急,走起来艰难、辛酸、无奈。上山时有奋发向上,步步高升之振奋,下坡时却是步步下降,一下下地滑向低谷。每跳下一个石坎,心便往下一沉。
刚产生去石井后山说书的念头时,充满期待、兴奋、激动,恨不得插翅直飞龙潭峡。已经走在路上,却不知怎么又调不住气,打不起精神,有点畏缩不前了。刚才一场小小的不愉快,像拔了气门芯的皮球似地泄了气,衰减了故地重游的兴致和激情。虽然早已熄火,和好如初,但银虎的埋怨声犹在脑子里转圈儿,挥之不去。细想想,人家说得不无道理呀。此去龙潭沟说书,有多大的胜算和把握?谁敢保这险?说实话,现在心里越发地没底儿了。想当年和王罗矿一走龙潭沟,半句书也没说,怎么进去,怎么退出。三年前和王小伟二闯龙潭沟,仗着道听途说得来的信息,以三天神书站住了脚,也算闯出点名堂,混得还可以。如今三走龙潭沟,连捕风捉影的说书信息都没有,打的是无把握之仗,无非是仗着人混得熟,关系铁,企图还有二走龙潭沟时的机遇和好事儿。但人走茶凉,何况已逾三载?不仅茶已凉透,恐怕早已变馊了吧?常言说,人在人情在,已隔三秋,人情安能延续至今?此去龙潭,不知深浅,或许乘兴而去,扫兴而归,一无所获,两手空空,亦未可知。一想到这,顿觉此行唐突,一时心血来潮,后果难料胜负。未出征,先落埋怨,如败仗,还不被银虎吐沫星儿给淹死?越想心越淡,越思意越寒,与其出力不讨好,倒不如早点拔马返回哩。转而一想,龙潭沟之行是自己发起,再说话吸回头[②]算啥事儿哩?好不容易把高银虎捺下,自己反倒心里起毛,再生枝叶,咋说哩这?算啦,决定了的事儿,是沟是崖都得跳,龙潭虎穴也要闯,何况只有龙潭,没有虎穴?
下了山,沿青河川西上,重走了当年的路。河滩里虽然鹅卵石略显磕绊、硌脚,但毕竟宽敞、平坦了许多,不用担心上下山路的掉沟、上墙或“滚坡[③]”。路好走了,银虎的牢骚就少了。一路无话,闪过红孩儿寺,左边儿一拐,久违的龙潭沟便映入眼帘。
三年没来龙潭沟,既熟悉又陌生,既兴奋又失望。景色和气氛感觉和原来有点不一样,产生了一些变化。悠然想起,三年前来龙潭沟,正逢盛夏,山花烂漫,郁郁葱葱,满目翠绿,充满生机。三年后故地重游,恰值隆冬,百草枯萎,万物萧杀,落叶凋零,触目苍凉,灰土土地了无生气。一溜溜通向山上的电线杆告诉我们,龙潭沟发生了大的变化,今非昔比,已经通上了电!电给龙潭沟人带来了光明,却给说书人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从各家各户房顶上的飞机天线,大锅来看,龙潭沟不仅通上了电,而且还拥有了为数不少的电视!唉,我们为了躲避电视,从前山逃往后山,孰知人家早已捷足先登,拦腰截断了我们的退路啊。
既来之则安之,想多了也无用,硬着头皮进村吧。
本打算上山找黑叔、秉哥他们的,三年了,迫切地想会会故交。但我们太累,实在走不动了,便打算先就近在骆村落脚。毕竟骆村也是熟地方,熟人也不少嘛,当年在这个队一连说了十一场书,也算是风风光光,吃得开,叫得响,混得还可以吧。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待走进骆村,才发现已经不再是三年前的情景了。三年前的骆村是夏季,树荫下,小溪边,男男女女,三五成群,欢声笑语。或乘风摇扇纳凉,或做鞋帮儿衲底子,或洗衣服、戏水,或东南西北、云天雾地扯闲话儿、拍说场儿……如今却是严冬,一切显得冷冷清清,鸦雀无声。大概天冷,人们都缩在屋里不肯出门吧。就连村子正中间的一棵大皂荚树下,最热闹、最红火的地方,原来是打牌,拉家常,做针线活儿的好去处,从早到晚都是聚满了人,现在却是一个人毛羽也没有,只有几块磨得发亮的青石条、青石凳闪着冰冷的光,让人看得寒心。若不是偶尔响起的几声犬吠,在提醒还有人类的存在,还真的以为这是经过鬼子大扫荡后的空村呢。
率先跳出来两只狗,虎视眈眈地盯着两个外来的不速之客,冲我们不友好地狂吠。这畜生丝毫不看我曾在这村说过书的面子,或许它们那时还没出生,压根没见过我,或许即使见过,也不认得了,因为狗眼总是看人低嘛。
狗叫声中,有一家大门“吱呀”声开了,有一个妇女探头向外打量,四目相对,似曾相识。刚想打招呼,人家却像压根就不认识一样置若罔闻,把我们当成了空气,回头“啪”地一声又关上了大门,让我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尴尬的“闭门羹”。
接下来又去找当初在这说书时哄得最热,帮忙最大的几个年轻小伙儿,铁哥们儿,结果一个也没找到,不觉心凉了半截。怎么办?还得厚着脸皮去找队长碰碰运气吧。毕竟人家是一村之主,正当家的。
打听到队长还是当年的那个队长,还是住在那个狭长的二进小院里。有所变故的是:队长他二婶,当初竭力阻扰说书,而又场场不离,赠给我蜂蜜,又垫补五毛钱书资,既可憎又可亲,那个脏兮兮的老太太已经不在人世。唉,再也听不到她的唠叨,再也喝不到她的中蜂蜜,花她的五毛钱,一辈子都感到是亏欠啊。止不住扼腕叹息,心里酸酸地伤感和失落。
去队长家是轻车熟路,到了门口,一边问着“有人吗?”一边径直摸了进去。进了二道门儿,队长夫人才从上房屋走了出来,看见我们,不冷不热地说:“我当是谁哩,原来是你们……”我问:“嫂子,队长老哥在家吗?”
“不在,去地啦。”简短地答复后,便没有了下文。既没下逐客令,也没有请我们进屋里的意思,甚至连个座儿也没有让。弄得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青石板上倒油,冷庆在那里了。队长老婆不善言辞,原来在这里说了十几天书,多和队长交道,和她没有说上过十句话。本来就不是太熟悉,时间长又隔生了,越发显得生涩、冷落了。人家没下文儿,我也没了词儿,一时显得十分难堪。
唉,今天运气不高,总是寻人者不遇。一连找几个熟人都不在家,寻队长又扑了个空。靠山山倒,指水水跑,弄得我一点儿也没招儿啦。
关键时刻还是人家高银虎,见我没词了,立马接住了话茬儿,与队长夫人仿佛一见如故,俨然老熟人似的,嫂长,嫂短,嫂鼻子,嫂眼,喊得那个甜味儿,那个亲热劲儿,打死我也学不会哈。高银虎拉家常,拍闲话,无话找话的本事让我自叹弗如。很快,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搭讪起来:“嫂子娘家哪哩?”“高庄。”“高庄都是姓高的呀,俺老家就是从高庄迁出去的。嫂子也姓高吧?”“嗯,姓高。”“哎呀,闹半天咱们还是一家子哩!一个高字掰不开啊。要是这,不能叫你嫂子了,该叫姐。”
这家伙,真能套近乎,也不论辈分,立马由嫂子改口叫姐啦。自己也摇身一变,由婆家兄弟变成了娘家兄弟,三言两语,便成了亲不溜丢儿的一家子。啥有姐弟关系近?娘家兄弟来了,当姐的岂有不招待之理?这一声“姐”喊得,成功地把我们让进屋里,坐到了火盆旁,烤到了暖烘烘的火,吃到了冒着热气的鸡蛋合苞捞面条,更重要的是,为找“姐夫队长”说书做好了铺垫,打好了基础。
中午终于等到队长回来。虽然队长对我们的到来表面上略显热情,内心不太痛快,但毕竟还是有几分交情,看几分薄面,况且又凭空多出个“内弟”,对说书的事儿不好意思一口回绝。尽管队里说书困难重重,压力山大,实在作难,可是推脱不掉,甩不离,只好硬着头皮,勉强地答应晚上说书。
晚上的书场仍设在村子正中间的大皂角树下。我们早早地吃罢晚饭,早早地做准备,除了拉桌子,搬板凳,掂开水之外,又多了一道工序,还得慌着扯电线,安喇叭,试麦克风等。一直忙到喇叭里响起了牛共禄的《搬龙角》,我们才得以喘口气。虽然费点事,有这个音箱设备,可以取代我们上场的一通敲鼓叫人,省了点劲儿。
喇叭比书鼓的声音大得多,传播也远得多,声势也强得多,但是招来的听众却不多。响了半天,才零零星星,稀稀拉拉来了十来个人,还都是上了年纪的“半不老人”。怎么叫“半不老人”?用农村话说,就是五六十岁左右的人,说老不老,说年轻不年轻,故为“半不老人”。眼见开书时间已到,听众却迟迟不见增加。我将疑惑和征询的目光投向队长。队长说:“开始吧,不用等,再等也等不来人啦。”
“人咋真(方言音‘震zhèn’)少?”我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队长。
“闲天时候,年轻人谁还在家?都出去打工了。家里都是些上了年纪行动不便的老人和脱不开身的引娃子妇女[④],大冷天的出不来门儿。即便有些年轻人没出去的,也是窝在家里看电视,谁想冒着寒冷出来听说书?” 队长说出的原因是实情,让人陡增许多无奈。
冬天的夜晚,适逢下旬,天上无月,仅剩下零零落落的几颗寒星,照着书场里零零落落的十来个听众,不温不火,不死不活,了无生机,一点也没有当初龙潭沟说书的热闹、红火、火爆。听众的热情似乎被严冬的温度降到了冰点儿,就连喇叭的声音在寂静的冬夜里也显得更加清冷、单调和苍凉。
来龙潭沟不能不见秉哥和黑叔,他俩是我的最念。不到黄河心不死,见不到秉哥黑叔我不甘心。第二天一早,就迫不及待地上山,翻前坡,越张沟,去会我那两个忘年交的好朋友。这次运气不错,很是顺利,如愿以偿地见了面。秉哥还是当年的那个秉哥,一如既往地热情,兄弟长兄弟短地叫着,拉着手久久不愿松开;秉嫂还是原来的那个秉嫂(没有换哈),手足无措地慌着烙馍、煎鸡蛋,激动得眼里噙着泪。这一切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把这两天的不快,不顺凝结而成的寒冰融化得一干二净。
倒是黑叔,似乎少了些当年的热心和激情,想想也是,快奔八十的人了,精气神和心劲儿已经大不如前,说话略显迟钝,走路有点拖拉。黑叔老了,更佝偻,更黑更瘦,脸上的皱纹显得更多更深,一说话就爱翻的白眼儿似乎略显昏黄、混浊,暗而无神。
黑叔对我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喜和热情。或许当初他订的杨家庄说书的事儿让我给推了,惹得不愉快,尚耿耿于怀;或许三年的岁月如流水,冲淡了当初的那一份好感和情谊;或许他年纪大了,不想再多跑闲腿,多操闲心,多管闲事了……想当年龙潭沟说书,黑叔既是神头,也是“牌官儿”,跑前跑后帮了大忙。可现在,再也不是从前那个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坚决果断的黑叔了。读着黑叔刻满岁月沧桑的脸,心里不由泛起一丝忧伤和愁绪
寒暄叙旧之后,还是切入了说书的正题。黑叔把昏黄的白眼珠有气无力地翻了翻:“咋说(书)哩?屋里都没人,即使有俩人,都看电视哩,不热说书的,说书谁听?没听家儿,昨收钱?现今不是过去啦,不好办呀。”
秉哥沉思了一下,把烟头一丢:“球啦!收不起钱就不收!老弟大老远风尘仆仆地赶来,总不能叫白跑一趟吧?咱心里能过意得去吗?咋着也得说几天(书)!不要紧,不就是三二十块吗?这钱我掏了。”
黑叔朝秉哥狠狠地翻了一下白眼儿:“这个钱你能拿起,谁拿不起!咋能叫你一个人出?算我一份,咱俩二一添作五!”我心里一热,满满的感激,当年那个豪爽、要强的黑叔又回来了。
两人商量了一下,从山上的北洼、后旮旯、驼腰、前坡、张沟这几个自然村来说,前坡村儿较大,人较多,位置相对较适中。为了照顾各村听书方便,拽更多的听众,决定书场仍然扎在前坡——还是三年前来龙潭沟首场说书的地方。
前坡还是那个前坡,书场还是那个书场,还是三年前说书的那个我。所不同的是:王小伟换成了高银虎,实力似乎增强了不少。三年前一面破鼓,一把烂弦儿,在龙潭沟打出了局面;三年后鸟枪换炮,拥有了音箱喇叭扩音器,可谓装备先进,设施完善,浩浩荡荡,可又能如何呢?
晚上的书场,我们比骆村说书更搁劲儿,把音响调到最大的声音,最佳的状态。段界平的《拉荆芭》,牛共禄的《竹林认母》轮番播放,这些可都是当时红遍豫西,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畅销河洛大鼓磁带啊。但是,如此有影响力的说书带子却吸引不了更多的听众,收不到预期的效果。我不甘心,认为播放磁带会给村人们造成是哪家在放录音机,而不是说书的错觉。于是,把小书鼓支上,弦子套上,又敲又拉的。鼓声,琴韵,通过扩音器扩出去,铿锵、嘹亮,在山谷中荡漾。声音在对面山上碰撞,折射回来。仿佛四周的山峦、峡谷都在击动战鼓、奏响乐章,纷纷响应,荡气回肠,群山为我助威,峰峦给我帮腔,好不壮观!
如此造势,期翼像三年前龙潭沟前坡说的第一场书那样,鼓声响处,前面山,背后峰,左边沟,右边洼惊现星星点点的“鬼火”,然后从四面八方向书场汇拢。那是远处村子里打着电灯(手电筒),提着灯笼来听书的山里人啊。我一边儿敲鼓,一边儿眼巴巴地东张西望,等着奇迹出现,然而,即使望眼欲穿,四面山谷依然黑黝黝、静悄悄,死一般地沉寂,看不见一丝灯光,听不到半点儿动静,让人沮丧透顶!再难现三年前山民们扶老携幼,举着火把,打着灯笼,翻沟越岭,跋山涉水,夜走十几里山路来听一场书的场景啦。说书还是当初的说书,听书人呢,都到哪去了?龙潭沟通上了电,有了电视,说书肯定受影响,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冲击如此巨大,让听众几乎消失殆尽是始料不及的。
前山说书受电视影响较大,才奔后山来的。殊不知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哪里都少不了电视的搅局。事实证明,电视在后山对说书的挤兑甚于前山。原因是:前山平川地带电视盛行已久,人们看得多了,也会腻烦、厌倦,产生审美疲劳,失去新鲜感,偶尔听场说书换换口味儿未尝不可。而后山刚通电,才有电视,人们稀罕得不得了,正在热乎劲上呢。有了电视这个香饽饽,谁还啃说书这个“黑窝窝”?所以山里人对说书再也热不起来了。
敲了半天鼓,不仅没把远处村子里的听众“敲”来,就连前坡这个小山村的十几户人家,人也没来到一半儿。骆村人口集中,听家儿还屈指可数,山上居住分散,书场里更加惨淡。每来一个听家儿,就好像抓着一根救命的稻草,点头哈腰地又是打招呼,又是让座。这时候,听书人是爷,说书人是孙子!
越是这种情况,说书越是不能泄气,得打起精神来,否则仅有的十来个听众也有可能被“说跑”,更让人下不来台。听家儿少,书还得说好,要不然书说砸了对不起秉哥、黑叔的一片苦心啊。
龙潭沟是熟地方,大家都知根知底的,我不能再像别处那样,把高银虎推在前头挑大梁,我缩在后面装徒弟了。但仍以他为主,我为辅。除了垫场,我也替他接一板正书,抵挡一阵。有的问,能接上吗?笑话!临阵磨枪,临场发挥,“就口气儿,耍把戏儿”,吃荆条屙箩头现编的本事早在跟刘大江厮跟时就学会了。谦虚一点说,对付一板书岂不是小菜一碟,信手拈来?何况高银虎拿得出手,能放到桌面上的书就一部《段官宝投亲》,不管到哪里,老是这一套儿,我耳朵几乎都听出茧子啦。所以,不是会说不会说,能接不能接的事儿,而是想说不想说,有兴趣没兴趣的事儿。偷懒耍滑得看场合,看地方,谦虚得过很就是骄傲,因为秉哥、黑叔的眼里揉不得沙子。
就这秉哥还笑着数落我:“老弟学滑了,年年轻轻可不想说(书),退居二线啦。”
我苦笑无语。想当初游龙潭,曾拍着胸脯向秉哥夸下海口,把龙潭沟的神话传说故事编成书,等再来时好在书场显摆。如今再来啦,编的书在哪呢?这两年河洛大鼓连连不顺,哪还有兴致编书?许诺变成了食言,以致这次见了秉哥没法交代,生怕被问及,没脸应对。好在秉哥大度,知道那是兴头上的狂话、戏言,指望不上,并没有深究哈。
人都说,舍命陪君子,秉哥却是搭着功夫陪朋友。晚上说书,白天没事儿,秉哥陪我到处转转,到北洼,到驼腰,到张沟,到当年说过书的村子,试图拾一下怀旧的情感。不看则已,一看则唏嘘不已。所到之处,满目凄凉,一片破败颓废之象。碎石铺就的村间小径已变得人迹罕至,几乎被杂草吞没,好多人家门上的铁锁已经生锈,房前落满残枝枯叶。此景此情,让人好不伤感嗟叹!
秉哥说:山上条件太差,交通太不方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话没毛病。可这些年林木繁衍得没有砍伐得快,野生药材越来越稀少。坐吃山空,资源枯竭,变成了穷山恶水。山上住不住人啦,好多家儿都搬下山,到条件好的地方安家落户。咱这差不多成了空村、废村。你哥我也在石井街买了房子,兄弟,再来龙潭沟咱们可能见不到面啦,得到石井去。
我黯然神伤。这才醒悟,在这里说书,不只是怨电视抢夺了听众,而是压根就没有多少听众可抢啊。
海有潮起潮落,人有时运高低,河洛大鼓亦然。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披靡,何等威风,却也有败走麦城,四面楚歌之狼狈。此次三闯龙潭,只所以败走麦城,究其原因,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占先。天时,严冬万物萧杀,说书遭遇寒流;地利,山高路远,说书举步维艰;人和,移民搬迁,电视分流,说书的找谁“和”去?
唉!
[①] 上悫山不用问路:河洛方言中的口头语,坑害或被坑都叫“悫”。上悫山,即被坑害。上悫山不用问路,意思为被人坑害问都不用问。
[②] 说话吸回头:新安方言土语:说出来的话又收回去了,戏指说话不算数,做事反复无常,不牢靠。
[③] 滚坡:新安土话,此处指不小心摔倒,从山上滚下来,称之为“滚坡”。
[④] 引娃子妇女:河洛方言土语。引:抱、带领、照顾、看护(孩子)。引娃子妇女泛指在家带孩子的哺乳期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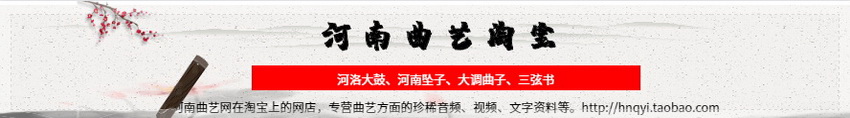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